2 0 0 3年由新华出版社出版的《善良女子的爱(中篇小说卷)———世界文学五十年作品选》一书收入了爱丽丝·门罗的中篇小说《善良女子的爱》。
李文俊:
不知道门罗很正常
当初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静群联系我翻译门罗的作品时,由于之前读过她的作品,也比较喜欢,一下子就答应了。花了半年时间将这部作品翻译出来。因为之前翻译过简·奥斯汀的《爱玛》,对于做女性题材的作品有一定经验,作为男性翻译,在翻译女性题材的作品上有一定难度,要求我在翻译过程中,尽量抛开男性的思维,以女性的角度去体味作品,用最优美的文字将原作翻译成中文,在这个过程中我也跟着去体味人生的悲喜。
对于很多人所说的门罗的作品在中国比较冷门的现象,也不能完全归因于一点。一方面,中国人本身读书的现状就不乐观,而今读书的人越来越少,门罗在获奖之前不为人所知属正常。事实上,门罗的作品确实很好,相对好多欧美作家,她的描写更加细腻,她笔下的人物经历的事情都不是人生的大喜大悲,她都是在进行平静的叙事,平凡的人物、平凡的生活,但看似平静实际暗流涌动,很有古典作家的风格,这种风格是我在《包法利夫人》、《复活》等名著中才能体会得到的。相对诸如《傲慢与偏见》等一流的女性主义作品,门罗的作品有过之而无不及。
作为一位长于女性题材的作家,成为加拿大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门罗的作品能够提醒人们尊重女性。门罗的书一直也不是畅销书、热门书,在此之前中国知道门罗的人比较少,对加拿大文学也关注较少,门罗的获奖也能帮助加拿大的女性文学作品进一步走向世界。
李文俊,著名翻译家,《逃离》译者。
丁林棚:
门罗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
爱丽丝·门罗的短篇小说形式比较特殊,在加拿大小说中是非常典型的,主人公都一样,相互关联,是一种linkedstories,她的短篇小说集基本都是如此。这种形式也是加拿大文学非常独特的一点,很多作家出名之前都写这样的linkedstories,她一生只写短篇小说,有十几本,只要提加拿大短篇小说,都会提到她,她是这种形式名副其实的代表,她得诺贝尔文学奖属于实至名归。
加拿大文坛如果要论影响力可能分两种,论外部有影响,当然是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了,她也拿了各种国际奖项,还有像去年因为李安的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大家知道得比较多的扬·马尔特,都属于外部更有影响力的作家。但是还有一些作家是国际上不大知道但是加拿大人非常赞同的,现实主义,写当地的人情世故,有一个和门罗非常接近的作家D avidA dam sR ichards,在加拿大有非常大的影响,被称为“加拿大的福克纳”,但出了加拿大就没有人知道。这样的作家还有很多,门罗是个代表。
门罗非常低调,不太愿意接触外界,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从表象上的影响力来看,门罗没有阿特伍德那么出名,英美读者当中估计也是更熟悉阿特伍德。阿特伍德和门罗也分属两个不同的传统,阿特伍德是那种国际化背景下的都市题材,女性主义的,关于生态的。但是门罗的文学就是写小地方、小人物,写她住的那个小镇,读起来很亲切,而且是半自传体的性质。女性啊,父母关系,母女关系,讲述故事时间打乱,又会给你留些空白,有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非常精彩。她的短篇都挺好,我记得她有一个短篇是讲她父亲怎么养狐狸杀狐狸的,把握生活的视角非常独特。从文学本质来讲是当之无愧的。
丁林棚,北京大学英语系副教授,加拿大文学研究者。
梁彦:相较于阿特伍德,门罗的争议更小
门罗获得诺贝尔文学后,整个加拿大的人都非常开心。所有大报头版都报道了这件事。但她毕竟已经82岁了,所以只是做了几个有限的访问,大致内容是谈了一下对自己得奖的感受,已及对短篇小说的看法。
门罗在加拿大文坛地位非常高,可以说是国宝级的。她同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可以称得上是加拿大文坛双姝。都是非常杰出的女性。相较于阿特伍德,门罗的争议还要更小一些。
门罗是一个非常谦虚的人。诺贝尔文学奖颁布时,他们甚至找不到她,因为她一直住在安大略省的一个小镇里,可能只有一两个人知道她的电话。后来他们找到了门罗的女儿,然后她女儿把她叫醒了。得知自己获奖后,门罗也非常意外,很吃惊,她说就像是做白日梦一样。当然,她也非常开心。
我最早读门罗,大概是十多年前,当时就被她吸引了。我觉得在描述加拿大小镇生活、平凡人的故事这个层面,没有人能跟她相比。在门罗的作品中,她不掩饰社会中的那些复杂和残酷,这就是她作品中的特点———大家看到的我也看到了,平实、微妙、精确。
门罗的写作是现实主义的,她早期很多东西非常朴实,甚至有一些平淡。在她的小说中,她并不是要讲一个故事,而是要描述生活中的一些细节,这是她在意的。所以在门罗的小说中,细节和情节是最重要的,故事反而是其次的。她追求的是,描述加拿大小镇的生活中,复杂环境下家庭的历史,以及细微的个人的经历。
所以她的写作非常直白,文风也不经修饰,直白而洗练。但这种简洁细微,又必须是经过多年打磨才能掌握,她创造了很多东西,包括她对故事的构思,总让人有冰山一角的感觉,就是她会描述一个事情,但是你会想象到后面很多东西。在这点上她是非常有天赋的。
在写作上,门罗像是一个敬业的工匠,她总会花很多时间去细细打磨。我曾经翻译过《巴黎评论》对她的访谈,她讲到自己每天都要写作,从早上8点到11点,基本上要4-5个月才能写一个短篇小说。一个星期7天是没有休息的。这一定是对这件事真正着魔后才会有的感觉。正因为此,她的每一句话都是经过斟酌的,要什么不要什么,材料的取舍,人物关系等细节。她的这种用心,让我在阅读她的作品时,时常会有非常直接的促动。
我没有见过门罗,但通过她在《巴黎评论》的访谈,我能感受到她是一个非常谦虚的人,像是一个“草根”作家。门罗不是学院派出身,也不属于成名很早,小时候家境很贫困,她很早就结婚了,然后有了自己的孩子,她和她的前夫,在小镇上开了一个小书店,就叫“门罗书店”,到今年已经50年了。
门罗就是一个家庭主妇,她甚至完全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她就是在坚持自己,一直在坚持写自己的东西。可以说,她完全就是一个文学的边缘人,她也从没有真正加入过什么文学的圈子。她在采访中曾说,早期,她很羞怯,她不知道怎么跟口若悬河、理论很多的出名作家打交道。时间长了就变成了一种选择。她曾说,如果很年轻时,跟这些人打交道,她可能都不敢继续写作了。她就是一个不大知道自己写作目的的人,也没有什么明确的写作计划。
而且她说作为一个作家,如果真有自知之明,没有谁会说自己的作品有多么好。对于她而言,写作之所以能坚持下来,是因为她没有过早接触文学的圈子。她曾说,如果你住在一个小镇上,小镇上连真正读书的人都没有,如果你觉得自己写得还不错,那你就认为自己是一个天才。
门罗今年已经82岁了,在今年7月,她过完生日后,接受《纽约时报》和一家加拿大媒体采访时,她说自己以后可能不会再写小说了,或许会写一些传记。其实她早在10年前,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便有了这样的想法。她当时说,自己年轻时,从没担心过没题材可写,只是因为要花时间照顾家庭,而没时间去写。到自己60多岁的时候,她开始觉得自己的写作激情和对写作重要性的看法都发生了改变,甚至觉得都不认为还有必要再像之前那样去做了。我估计她以后应该不会再写小说了,毕竟年纪也大了,至于传记,她应该还是会写的。
梁彦,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记者、即将出版中译本的《巴黎评论·作家访谈Ⅱ》门罗部分的译者。
薛忆沩:
说门罗是“契诃夫”低估了她
门罗是当今世界上极少数坚持“只”用短篇小说这种体裁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她37岁那年出版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就获得了加拿大最高的文学奖。随后她的文学道路可谓一帆风顺。她的全部作品由14部短篇小说集构成。这些作品语言细腻、形式精致、内容深刻智慧,在英语世界享有盛誉。门罗的写作专注于女性,但她的视野却又非常开阔,她要发现的不是女性的隐私,而是人性的秘密。
说门罗是“契诃夫”,从作品的数量和题材的广度上似乎还有点低估了门罗。而在数量这么大的情况下,所有的作品都能够保持极高的质量,这也有点不可思议。另外,门罗的作品也更具有“现代性”,在美学上的追求也更为自觉和大胆。短篇小说在当今世界上几乎是没有市场的,而门罗却能够近50年不变,逆市而动,用传统的体裁征服现代的读者,称她为“在世最伟大的短篇小说家”一点也不过分。事实上,她在短篇小说中的位置很可能是“后不见来者”的。
现代的创作技法对门罗就好像本能和直觉。“时空转换”、“打碎重整”在她的笔下没有雕琢的痕迹。对现代创作技法的熟练运用扩展了叙述的空间。所以,门罗的短篇小说往往有长篇那样的分量。想起来,门罗可能是西方女性严肃文学作家中学历最低的作家。但是,她的作品中同样充满了精辟的智慧和强烈的美学追求。
薛忆沩,知名作家,现居加拿大。
刘意青:
门罗是每个人都能读进去的
爱丽丝·门罗在加拿大文学中成就是比较出色的,大家都熟悉阿特伍德,她年龄比阿特伍德大,有点像前几年多丽丝·莱辛得奖。我很喜欢她,活到这么大年纪,能得诺贝尔文学奖,我替她感到高兴。
加拿大文学史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出了不少优秀的作家,像写《英国病人》的迈克尔·翁达杰。特别有意思的是在加拿大,女作家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像阿特伍德,像玛格丽特·劳伦斯,像卡罗尔·希尔兹,还有门罗,都是很优秀很出色的作家。当然她们的流派不太一样,阿特伍德比较现代派,童话的格局,政治性、寓言性的故事,阿特伍德创作也很快,一年一本,她做历史和社会调查之后就能编出故事。
但是门罗和阿特伍德很不一样,门罗非常朴实,就是写加拿大拓荒期过来的女人的经历,她们的情感,她们的宗教,各式各样的经历,非常细腻。譬如她讲黛儿这样一个小城镇女孩,她老师的故事,她的第一次爱情的经历,她的宗教信仰,她怎么走出这个圈圈作为艺术家的道路。她用非常娴熟的艺术笔法活生生描述加拿大的历史阶段,个人特别是女人的故事,怎么成长,牵涉到很多矛盾、很多奋斗。不是有人把她比作契诃夫吗,她自认受契诃夫影响很深。她的东西你看了以后会觉得语言非常清澈流利,人物非常鲜活,就是我们身边的,加拿大人可能更感觉就是他们乡土的事情。
我给英语系的学生教了近十年的“加拿大文学选读”,门罗的作品选篇一直在教,我是感觉她的英文可学得多,对学生英文的帮助比很多美国作家的作品好得多。有些小说更多是为批评家写的,代表最试验性的东西。但是门罗不是这样的,她经得起批评家的掂量,却也是每个人都能读进去的,而且在里面看到了自己。
门罗在后现代的今天,为什么这么晚才被承认,她不是福克纳他们那样一出来就让人震惊的,她就像醇酒,慢慢的,但是最后味道却越来越醇厚绵长。
刘意青,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加拿大文学研究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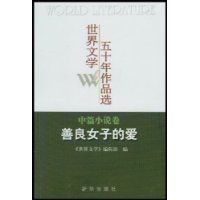




发表评论前,请先[点此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