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卡伦·霍妮(1885.9.16-1952.12.4)
德国心理学家,新弗洛伊德学派研究者。对基本焦虑研究贡献良多,并提出理想化自我的心理学概念。她是社会心理学最早的倡导者之一,相信用社会心理学说明人格的发展比弗洛伊德的性概念更适当。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作者:(美)卡伦·霍妮 著 叶颂寿 译
出版时间:2013年01月
为了欲望,为了安全的需要,有时人们会认同、顺服、屈从某些自己也并不相信的东西,但最后总要付出极高的心理代价,因为他无法避免激烈的内心冲突。
我一向喜欢具有社会文化视野的心理学家,因为他们能看到人的行为、人的所谓“心理问题”的复杂性。他们不会简单地将问题归结于人的童年经历就了事,而愿意去了解人的内心的冲突是怎么建构出来的,在其中社会文化起了怎样的作用,他们又是如何与之抗衡的。
套用波伏娃的“女人不是天生,女人是变成的”,我们也可以说,很多“心理问题”不仅是被社会文化催生的,也是被社会文化建构、界定出来的。现实生活中不乏这样的例子:一些在中国学校被当做“问题学生”、自己也自暴自弃的孩子,到了国外竟神奇地恢复了自信,变成了阳光少年。具有这样视角,或许更能跳出技术化的陷阱,同时也更容易转换视角,将“问题”看做是一种对文化,特别是病态文化的对抗与斗争。
比如,一个网络成瘾的孩子,何尝不是在用这种方式,对抗学业上的挫败、人际上的孤单、对人生的迷茫、自我价值感的低下和日常生活的无趣与无聊?只是,如霍尼所说,这种方式会让人“付出高昂的代价”,“使他的生机与活力受到损害,使他的人格拓展受到阻碍”。但心理治疗师若能看到在这种不健康的防御机制下,还埋藏着这么多复杂的东西,看到孩子真正想反抗的是什么,不仅更能找到问题的核心,也能帮助孩子重新来看待自己,看到那些渴望和期待的宝贵,看到自己不愿意对病态文化屈从,从而重新建构自我认同。在这个基础上,孩子才可能改变他和“网瘾”的关系。
“我们”时代的神经症
霍尼在书中提出三种神经症的文化来源:竞争所带来的敌对性紧张,即以竞争和成功为一方,以友爱和谦卑为另一方之间的矛盾;各种需要所受到的刺激和满足这些需要时受到的挫折,即被刺激起来的需要(如高消费)和实现之间的差距;个人自由和所受到的局限之间的矛盾。
将时空置换到今天的中国,也许我们也可以问问,“我们”时代的神经症有哪些?有没有弗兰克所说的“集体的神经症”呢?有哪些社会性的现象,其实正是“集体神经症”的表现呢?造成这些神经症的社会文化因素又是什么?
无疑,霍尼所提到的“时代”的、“集体的”神经症,无论是症状还是原因,在当下中国都有丰富的体现。
比如,日渐庞大的“国考”队伍,年轻人从“逃离北上广”到“逃回北上广”,这些行为背后掩藏着怎样的焦虑?是不是年轻人越来越感到只有进入体制才能获得安全感?是不是小地方“拼爹”的文化,让他们宁愿承受大城市的生活压力,也不愿意在缺乏公平公正的环境中生活?这样的选择会不会带给他们巨大的内心冲突?
和过去相比,现在的中国家长显然更为焦虑,无论是为了孩子到县城买房的农民,还是想尽办法为孩子择校、周末筋疲力尽带着孩子赶各种班的城市家长,他们的焦虑是否是面对教育不公而又无奈的一种行为反应?
网络上的种种人身攻击,是不是恰好反映出,我们严重缺乏被尊重的经验,却经历了太多的被排斥、被歧视,甚至是被侮辱、被损害,因而只有将他人贴上标签,甚至视为猪狗,才能显示出自己的高贵?
还有另一种更加隐蔽的情况,如霍尼说的“有许多人,虽然表面上看完全适应现存的生活方式,但实际上却可能有严重的神经症”——为了欲望,为了安全的需要,有时人们会认同、顺服、屈从某些自己也并不相信的东西,但最后总要付出极高的心理代价,因为他无法避免激烈的内心冲突。
用什么治愈我们的焦虑
为了克服内心的焦虑和不安全感,人们急切地要抓住一切可能抓住的东西,从刚参加工作就要买房,到对权力、金钱、名望的渴望,甚至是对“食色”的过度贪恋,最后一招就是用脚投票移民海外。
以我看,中国人的种种集体神经症,不排除传统文化对我们人格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无法感受到作为人的自主性,无法感受到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预期和把握的。对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未来无能为力、无所适从,那我们又如何摆脱内心深处的不安与焦虑?
正如崔卫平女士所说:“一个人要想活得舒坦舒心,不仅仅是理顺与他自己的关系,还应该包括理顺他和这个世界的关系,与这个世界的关系不顺,感到无法进入这个世界,即使在私人生活中把自己照料得再好,给自己找出再好的说辞,心中仍然有一处是空洞的,不能填补的。”
当然,每个人也需要对自己的生活承担起责任,包括承担起公民的责任,从自己做起来改变那些使我们焦虑不安的、压抑的、冲突的社会文化,而不是像神经症患者那样,沉溺在“受苦”之中,使自己更加不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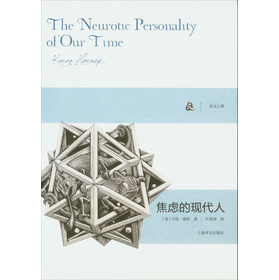




发表评论前,请先[点此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