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文学青年大概都背诵过卡夫卡的这句话——“你活着的时候应付不了生活,就应该用一只手挡开点儿笼罩着你的命运的绝望,同时,用另一只手记下你在废墟中看到的一切。”我背诵过这句话,并且有点儿偏执地认为,许多写作都出于某种“命运的绝望”,几年前我看到美剧《绝望的主妇》,开头第一句旁白——每一个男人都在平静的绝望中度过一生。这句话也可以用来描述卡佛的小说,平静的绝望。
阅读《雷蒙德·卡佛——一位作家的一生》,我的出发点就是想知道,卡佛那种绝望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那种绝望又怎样促成了他的写作。1954年1月25日,卡佛的家乡,亚基马的《每日共和报》发表文章,通栏标题是——海明威丛林归来,小说家结束环球之旅。报道说,海明威“像他笔下那些胸毛浓密的男主角一样充满危险地生活着”。卡佛说,读那篇报道,就让人陶醉、兴奋和刺激。他曾幻想,并且真的向妻子提出来,去西班牙住几年,找到一个阳光充足的地方,生活并写作。“对于他这样背景的人来说,过一种海明威似的生活无疑是个幻想,他会牵挂自己的家庭,他的冒险应该在家里进行”。原谅我岔开话题,说到文学青年的一本 “圣经”级读物——海明威的《流动的盛宴》,他和他年轻的妻子住在巴黎,在巴黎的咖啡馆里写作,这是无数文学青年的白日梦。遗憾的是,卡佛只能呆在家乡, 在工厂上班,星期天晚上,打了一天野鹅之后,卡佛坐下来写诗。这样两件事——在荒郊野外游荡,在内心世界巡游找到支撑自己的文字,同时发生在卡佛身上。
卡佛报名参加了好莱坞的帕尔默写作学院所开设的函授课程,支付了首期二十五美元的学费。卡佛作品的基本长处大多没有超出帕尔默教材第一册的范畴——把读者放在小说人物的位置上,描述简练。卡佛说,“作为小说家的素材,现在打动我的大部分的东西是在我二十岁以后出现的,我确实不记得身为人父之前的许多事情。在我年满二十岁以及结婚生子之前,我真没觉得我的生活中发生过什么。然后,事情开始发生了。”事情是什么呢?体力劳动,低收入,酗酒的父亲,要养育孩子,太年轻的妻子,卡佛自己也太年轻了,也喜欢喝酒。卡佛的一位学生这样回忆——如果说烈酒是汽油,他的两个孩子则是火柴,有好多年,他的生活都有焚烧一空的危险。雷和他的第一任妻子玛丽安·柏克在还不到二十岁时,就生了两个孩子,他后来在随笔《火》(Fires)中,说两个孩子对他的写作影响最大,“是种沉重而有害的影响”。他用了那样的词。
《雷蒙德·卡佛:一位作家的一生》
点击图书封面可在三大网店购买
出版社:龙门书局
作者:卡萝尔·斯克莱尼卡 著
译者:戴大洪,李兴中
出版时间:2011年12月
家庭的负担让卡佛感到沉重,不过他坚信,只要做正确的事情,坚持不懈地做下去,就会有好的结果。这里所说的“好的结果”,从精神层面来说,是打造出完美小说的艺术;从物质层面来说,是把小说卖出去。不过他的第一位写作老师加德纳告诉他,凭借文学写作来赚钱几乎不可能。加德纳还说,宁可使用那些普通词汇也不要使用“貌似富有诗意的”词汇,要认识到言简意赅的重要性。他的第二位写作老师理查德·科尔特斯·戴,在卡佛身上看到了写作的才能,他认为,一个作家需要的是,叙述的意识,用细节建立某种存在的技巧,还有如何表达,“表达是一种真正的才能,是一个人能够成为一名作家的可靠标志”。他告诉卡佛,为了得到小说素材,他应该更密切地关注家庭。于是卡佛开始描写工人,描写养育着孩子的夫妻。在卡佛的工厂里,有一个叫韦德尔的聋哑人,大家都叫他傻瓜,口袋里装着卫生纸,他的工作之一就是给厕所补充手纸,他经常受到大家的戏弄。他把大量时间消磨在工厂的池塘边上,一边喝啤酒一边钓鱼。卡佛根据韦德尔的遭遇写了短篇小说 《傻瓜》。
卡萝尔·斯克莱尼卡这本卡佛传记厚达六百余页,我疑心,这本书比卡佛所有的小说加起来还要长。在这本传记的头几个章节,作者详细地描述了卡佛所上的写作课,包括阅读书单,讨论和修改的细节,以至于读者像跟随卡佛一起上写作课似的。在卡佛之后,我曾经读过好几位美国作家的短篇小说集,不客气地说,我几乎闻到了他们上课时教室里弥漫的那股狐臭味道。没错儿,写作可以讲授,写作也有技巧,但按照那种写作班套路写出来的小说,有一股做作的匠气。还要不客气地说,卡佛小说中有不少平庸之作,那是他的习作,他在写出完美作品之前,进行了大量的练习。这些习作的毛病在于,你看不到想象力,似乎写作只是寻找到生活中那些可以称为“素材”的东西,然后找一个场景,用上足够的细节,把现实生活提炼成一篇小说。你看不到那种穿透生活迷雾的想象力,也许卡佛那种绝望的生活扼杀想象力。卡萝尔这本传记,最让我难以接受的是,她也在扼杀想象,她像大侦探波洛破解谜题一样把卡佛小说一一解释了一番。小说是一个迷人的呈现,好小说让人着迷,读者为作者的想象力和独特的表达着迷,就像观看一个魔术师从魔桶里不断变出兔子、鸽子。我们读小说的时候也沉迷于这样的表演。而作家传记多多少少都是专门给人败兴的,把魔桶翻个底儿朝天,告诉你里面暗藏的机关。卡佛这本传记的作者在“败兴”上做得实在是太尽心尽力了,她访问当事人,运用资料,恨不得要告诉你,卡佛的每一篇小说都是怎么来的,生活中的哪一段经历构成了他最初的“素材”,他又是怎样裁剪,把那些素材弄成了小说。
我说不出为什么会喜欢《大教堂》这篇小说,那个盲人在画大教堂,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小说的伟大就在于这种开放和复杂。但是,这本传记会告诉你,有个叫加里格尔的家伙,曾经为一个叫卡里沃的家伙工作,那个叫卡里沃的家伙是个盲人,在西雅图警察局工作过,在纸上画过画儿什么的,然后卡佛结识了他们,写出了初稿,编出来看电视、讨论大教堂之类的情节。小说读者为什么要知道加里格尔和卡里沃是谁呢?为什么要知道《傻瓜》里的韦德尔是谁呢?小说创作是一种魔术,经不起传记作者这样的分析。
卡佛小说的一个独特魅力是情感的浓度,他的学生记录下他说过的一句话:“一个短篇小说、一部长篇或者一首诗应该产生一定次数的感情冲击,你可以从冲击的强度及次数上,来判断这部作品水平如何。”如果以这个标准来衡量,《卡佛传》的情感浓度小了点儿。当然,卡佛的故事并不那么简单,一个贫困的文学青年终于成功,获得教职,获得津贴,能够在一流杂志如《大西洋月刊》、《老爷》上发表文章。文学是一个失败者的行业,一个成功的小说家最终不过是获得了他骄傲地宣称自己是一个失败者的权利。在卡佛一本成功的小说集要面世的时候,他正因经济纠纷面临审判,他的妻子在法庭上这样辩护——“法官大人,总有那么极少数人,为了真实地切实体验我们大家的感受,他们不得不凝神专注于自己的阴暗面。我的丈夫,就是这些该死的倒霉的人中的一位,拜这种责任所赐,他既要受苦受难,还得心高气傲。他嗜酒如命,大约一半时间生活在与小说相应的世界中。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在现实世界中辨别是非并据此行事的能力衰退了。”这桩小小的经济纠纷可以看作是作家贫困生活的延续,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象征。哈代说,在文学上,年轻人常常从当法官开始,只有当智慧和经验到来时,他们才终于获得了受审的资格和尊严。卡佛的《请你安静些,好吗?》出版,《纽约时报书评》给出了高度的赞扬,卡佛终于获得了“受审的资格”。
卡佛继续写他的小说,那种绝望的气氛并没有散去。这本传记堆砌了大量的事实(有点儿淤了的事实),无关紧要的细节,来讲述卡佛的创作生活。这让我想起另一本极其抽象的书,克尔凯郭尔的《致死的病症》,哲学家讨论的也是“绝望”,他说,绝望是这样一种病症,得到它是一种上帝所赐之福,从未有过它是最大的不幸。绝望并不是寄希望于一种尘俗的困顿、一种现世的苦难是可能被消除的,绝望的自我是一个承受着的自我,持之以恒地建造空中楼阁,一个处于绝望中的人幻想,他的幻想又去和感情、认识、意志发生着关系。许多人都多少带着一点儿绝望生活,少数人才经由绝望达成精神上的自我。在我看来,《致死的病症》是一本更出色的作家传记,它从精神上阐述问题,你可以用它来解释卡佛。这远比在他的生活漩涡中找出他创作的证据更有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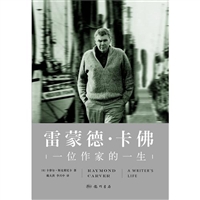







发表评论前,请先[点此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