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代周报记者 李怀宇 摄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余英时 著
出版时间:2013年06月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作者:余英时,汪荣祖,等 著
出版时间:2013年10月
《余英时别集(全四册,中国情怀、卮言自纪、学思答问、师友记往)》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余英时 著,彭国翔 主编
出版时间:2012年04月
余英时先生今年83岁。一辈子研究历史,结果“返璞归真”。对中国的将来,他不再执著于预言某个特定的时间:“在这样一个大变动中,某种新的秩序的建立不是短期的事情。”相反,他强调偶然之力:“历史是偶然加成的,没有什么必然的规律之类。人生也有许多偶然,你根本没有办法预料,自己也控制不住自己。”对不可知的未来,余先生唯一强调的是自由;对年轻人,余先生的建议更像警示:“把自己当人。”
陈寅恪诗云:“读史早知今日事。”读史能否预测明日事?史学家唐德刚有言,一部中国近代史,便是一部近代中国政治、社会、文化的转型史,他将这两百年的转型期称为“历史三峡”。唐氏的时间表是1840年到2040年,期望走出“历史三峡”之时,国家风平浪静,百姓可以过点太平日子。李慎之则曾预测:中国成功转型的时间会在2040年。唐、李两人谈到的时间不谋而合,引人深思。
史学家余英时认为:“为什么两百年就一定解决呢?是大家把自己的希望混在历史发展中间去了。至少我不可能给出什么时间表。两百年走出历史三峡,这是形象化的说法,没有科学根据,只是表示某些人有这样的希望。在我看来,在这样一个大变动中,某种新的秩序的建立不是短期的事情。”
对预测未来世界,余英时说:“那是希望的投射。因为大家有同样的希望,希望太平,希望永久的好的秩序出现,以后就是安安定定过日子。这是人的正常愿望,但是整个历史是许多不同的势力在冲突、演变中,有合作,也有冲突,没有办法判断往冲突的地方走,还是往妥协的地方走。”在余英时看来,研究历史的意义就是了解为什么造成这样的现象。“了解多了,就晓得这些过程对长远有一种智慧的启发性。不是说某一个人看某一本书就跟着改了,会避免从前的错误。但是长期讲,可以产生一种智慧,这种智慧对全体社会来讲,社会越进步,还是可以起作用的。有些人有些事是不能做的,一做公众马上就群起而攻之,这个智慧社会上已经存在了。”
余英时认为,大到社会演变,小到个人生活,都有许多无法预见的偶然因素决定。“历史是偶然加成的,不像有什么必然的规律之类。人生也有许多偶然,你根本没有办法预料,自己也控制不住自己。”有些历史学家自认穷其一生就是要在历史中寻求规律。余英时说:“现在西方史学家百分之九十九没有在找规律了。社会上有一个现象,把这个现象搞清楚,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在这个地方发生?前因是什么,后果是什么,中间的过程是什么?就是要了解这个真实性。”
为什么许多人研究历史是想知道未来?余英时说:“未来不可知,因为长期不大动的社会,可以从过去的经验里得到一些教训。实际上得不到什么教训,司马光写《资治通鉴》,就是要给皇帝找教训的,皇帝真的能得到教训吗?皇帝也有七情六欲,等到七情六欲作主的时候,什么教训也忘了,他明明知道女色有害,突然爱起哪个女的来就不顾一切了。他还管教训不教训呢?他把皇帝的责任感给丢掉了。有人说,读历史是要从中得到经验,那是很陈旧的观念。”
《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当中有很多精彩的记录,可是事隔千百年后,司马迁写起来好像是亲身在现场记录一样,到底可信吗?余英时说:“这当然需要旁证和辨别,我们读史书一定要有怀疑的态度,不能一看作者是大家,就全盘接受了。不过,这也涉及到历史的想象力问题,司马迁运用了想象力来重构历史。史学家的想象和小说家的想象是极其相似的,不同的是史学家的想象要在一定的时空之内,并且必须受到证据的限制。你看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就通过丰富的想象力,使明清的兴亡遗事复活了,书中的重要人物好像重现在我们的眼前一样。他们的喜、怒、哀、乐,以至虚荣、妒忌、轻薄、负心等心理状态,我们都好像能直接感受得到。我写《朱熹的历史世界》,也是尽量根据大量可信的证据来重构朱熹的历史世界,希望使读者置身其间,仿佛见到历史人物在发表种种议论,进行种种活动。”
在历史与现实世界上下求索,著书立说的乐趣何在?余英时说:“还是为知识而知识。没有一定的目的,本身就是一种乐趣。就等于喜欢下围棋,就什么都不会想,只想在棋盘上怎么进行变化。打麻将、打桥牌恐怕也是这样。为艺术而艺术,为学术而学术,为真理而真理,本身就是一种乐趣。人类讲真理,过去西方最重要的是讲真、善、美,求真、求善、求美,都是没有目的的。对人家好,并不是希望人家报答你,而是说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应该有善意,不应该想害人,能帮的应该尽量去帮他。这就是从前一句老话‘助人为快乐之本’,我的快乐从哪儿来?能帮助一个人,心里是最快乐的,并不再有其他想法了。求真善美是人向上的力量,我们并不只是一个动物,就是吃饱饭,穿好衣服,住好房子,坐好汽车。人一定要有精神要求,宗教最高的追求是真善美。”
“尊重不同,才能和谐”
时代周报:身在海外,你对祖国的未来有什么期待?
余英时:我们在海外当然希望中国变好。现在海外是一个和平的看法。中国的许多事情是在酝酿中,所以我们看不清到底是怎么发展的。我不能给中国的未来安一个时间表,以后几十年中国的发展,我不知道。要开放才能真正稳定,讲和谐社会不是很容易的。和谐的前提就是承认不同,尊重不同,只有不同才能和谐,和谐不是保持一致,否则就是强制一律,反而会造成不和谐。
外国有各种的猜测,这是不可靠,谁能说五十年以后会是怎么样的?现在各种地方势力多了,城市和乡村的距离越来越大,这些都是问题,将来谁也不知道怎么发展的。未来中国的变化没法预测,我希望中国好。
时代周报:中国市场的高速发展会引发什么样的观念变化?
余英时:现在只看市场是不行的。在中国能赚钱还是因为廉价的劳工,这就是许多外国人愿意去投资的原因。有廉价的劳动力当然东西就卖得多,所以经济增长率很高,那是不错的。但是美国是相当平均的,没有哪个地方城乡差异或者南北差异那么大。美国只有百分之五的人口从事农业,城市吸收农村的劳力。过去中国少数人的生活不错,很安定,不过那时候农村生活简单,欲望也不高,现在欲望高得不得了。最近有人去我的安徽乡下,回来告诉我:年轻人都没有了,都出来打工了。这在我们从前是没有的事情,哪有几个人到城里去找工作的呢?
我觉得民主和自由是整体秩序与个人发展的关系。没有自由,不可能发展。美国唯一的好处就是换一个政权,不需要流血作为代价。从前胡适就对国民党说:实在不行,一党就分成几党好了,自己竞争,这样就实行和平转移。国民党那么强势,在台湾被选民一选就选下去,第二次再选不行,但至少还有机会。如果说霸道能控制局面,短期是可以的,看看历史上,希特勒威风凛凛的时候能够维持多久?这是靠霸道,最后是自己给自己挖坟墓。我们现在要平和一点看这个世界的变化,也希望自己在文明上赶上别人,不是说发点财就变成暴发户的心理,没有文化。文化要有价值,社会公平就是价值之一。
时代周报:在社会财富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如何树立健康的价值观念?
余英时:价值的问题不能说马马虎虎,把别人的财产无缘无故没收过来。中国说法是“藏富于民”,财富在民间,百姓会好好保护:我创造财富,不会把这个财富浪费的。我记得美国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穷人没有地方住的话,政府要管,管到最后穷人跑到最贵的旅馆,那就不可能负担。有一批人控制公家所有财产,这批人难道都是圣贤?权贵资本主义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还要受各种各样的限制,在法律上征收很多税。像美国很多的资本家最后设立基金会,回报社会,用于研究学术、艺术各方面。钱没有由个人浪费,这是一种心理上的满足。资本主义也接受许多所谓社会主义原则,就是所谓福利国家的问题。但是这些国家也有问题,就是保守主义出现,因为穷人完全不做事,也可以让国家养,社会养那么多懒人,工资比拿福利还少,人家就不干了,就没有人生产了。这是永远不能解决的问题。
一个国家,政治比重应缩小
时代周报:在中国历史上,如何处理权力制衡的问题?
余英时:中国是大一统的政府,没有相对的力量可以跟它平衡,中国没有像西方基督教这样的宗教。在西方中古时代,想做皇帝,要主教同意,要教皇承认,教会与皇权是相并列的,所以皇帝不是至高无上的。
中国只有士大夫提倡道,这个道没有组织宗教,佛教、道教都是地方性的宗教,没有全国性的组织,怎么跟一个有全国性组织的王朝平起平坐呢?没有这个力量。但是中国儒家已经提出道、理的观念,让皇帝不能做过分的事,因为王朝还是要靠士大夫来维持的,中国完全是皇帝一个人胡作非为也不是事实,这就是说文化还有一个控制的力量。明朝李昆讲:朝廷之上,士最大;理又比士大。中国儒家讲的道理有限制皇权的意思。明朝有一个姓和的太监反对皇帝,皇帝气得不得了:“是哪个指使你的?”“有两个人指使我,一个是孔子,一个是孟子。”有某一种权威,皇帝也不敢冒犯。
中国不是没有精神力量,但是没有组织的精神力量。我到比利时去看国都,国会上写着工会代表、商人代表、封建领主代表,都是对皇权加以限制的。英国的大宪章就是地方诸侯要限制皇权,这是在12世纪,中国是在宋代的时候。换句话说,社会要有多种势力,皇权就相对减低,所以南北朝皇室的力量弱,大族的力量强。有人说,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如果真是封建,皇权就受到限制了。日本是真的有封建,所以它的皇室并没有力量。中国吃亏在没有封建,封建消灭得太早,就没有东西可以跟皇权对抗了。社会上有大的势力,皇权不得不低头。一个人统一了天下,贵为天子,为什么要受限制呢?这不能骂中国不行,因为是许多历史因素造成的。不是哪个皇帝本事特别大,就可以在中国胡作非为,这是有社会基础的。
时代周报:在现代化文明的进程中,如何通过法制健全等方法来减少暴力?
余英时:现在如果要开创出一个局面来,可以不断地改进。改进是唯一的办法,不是靠革命来解决问题,尤其不能用暴力,不能用杀人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
中国还能经得起再来一次革命吗?美国和西方社会主要是靠法律。美国社会最坏的犯罪分子也要有人给他辩护,而且判罪也不是由法官来决定,有一个陪审团,陪审团认为有罪,才能定多少罪,如果认为无罪,明明是犯罪的人,也照样释放。我们现在希望中国的老文明能够更新自己。
时代周报:你希望中国的发展朝什么样的方向前行?
余英时:我认为要把政治的比重在一个国家里变得很小。在中国历史上,谁胜利就要拥护谁,百姓就变成顺民了,没有批判能力就是顺民。这种演变趋势是出现一个特权阶级,而这个特权阶级一定要维持它的统治,这是最糟糕的。我们希望中国是一个开放的社会,能够自己慢慢调整。从美国黑人的发展历史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开始的时候黑人被压迫得不得了,这几十年来黑人地位不断上升,黑人可以竞选总统了,这就是进步的地方,不要以为是小事情。这就是靠自我调整,如果一个机构不能自我调整,必须外面把它打败了才能取而代之,这就危险了。
时代周报:在变革时代,你对年轻人有什么建议?
余英时:我想这些问题你们不要太担心,但是自己要努力,要自己把自己当人。我认为每个人要争取自己基本的人权,不要随便被人剥夺了。如果人家给你恩赐,就感激涕零,就不太好了。我们不是为一个人活着,也不是为一个组织活着,我们是为自己活着,这是最要紧的事情。人就应该量才适性,自己有多少本事,在什么环境,尽量做自己该做的事。但是人不能光为自己着想,我们念中国书,受中国文化影响,不能就只管我一家,其他就不管。因为小时候受影响,有社会责任感,但是责任感也不能无限膨胀到连家都不顾了。起码的责任是对家里人有承担,这以后才有余力为公家做事,这是很简单的人生道理,做到这一点,中国才能够慢慢走上现代社会,只能求一点一点地变。
余英时
安徽潜山人,1930年生于天津。1950年至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陞先生,获博士学位。曾任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著有《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士与中国文化》、《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朱熹的历史世界》、《重寻胡适历程》、《未尽的才情》、《会友集》、《中国文化史通释》、《情怀中国》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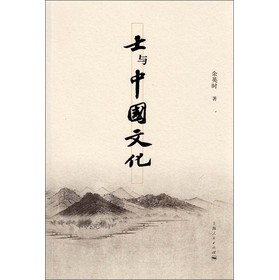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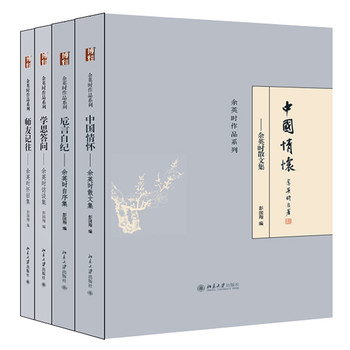




发表评论前,请先[点此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