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永嘉在书房。

朱永嘉注释的《唐六典》、《吕氏春秋》等古籍。另一位注释者“萧木”实为王洪文秘书肖木。当时,朱、肖都属“敏感人物”,出版社不得以用了化名,朱永嘉所编另一套丛书《传世藏书》署名“朱允佳”。

朱永嘉所藏《资本论》,“文革”后期购买,在监狱中重读,内页写有当时的读书笔记。

“文革”期间,“上海市委写作组”在朱永嘉领导下,编选了这套文艺丛刊。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作者:朱永嘉 著
出版时间:2012年05月
《商鞅变法与王莽改制(复旦老学者朱永嘉论史作品,重启改革话题)》
出版社:中国长安出版社
作者:朱永嘉
出版时间:2013年07月
出版社:中国长安出版社
作者:朱永嘉 著
出版时间:2013年04月
83岁的朱永嘉住在复旦大学第一宿舍一号楼,这是一栋两层的老建筑,木式楼梯,顶层有阁楼。上世纪30年代日本人建好之后,这里住的是日本校级军官,二战胜利之后,复旦大学系主任以上的人才有资格搬到这里。朱永嘉提起,当年的复旦老校长陈望道就住在旁边的17号楼,1947年陈望道还是新闻系主任时,全市大逮捕,陈望道就在这里保护过“左派”的学生,让学生躲过搜查。当朱永嘉搬到第一宿舍时,已经是“文革”初期的冬天,随后他因领导上海市委写作组而在政治上风生水起。如今,房子已旧,老屋里满满当当住着他和儿孙三代人。
朱永嘉的书房在一楼。昏暗的光线下,书房里一股陈旧的气息扑面而来,一角的柜子上摆满药片,紧贴两面墙的书架直抵房顶,藏书书脊大多已经磨损,有的落满尘埃。两张简单的老式红漆木桌搭在一起,上面也挤满了资料和书籍。主人扭开电灯,屋子才稍显亮堂,颇有些青灯黄卷的意味。来访时临近晌午,朱永嘉家里保姆正在不远的厨房准备午饭,油花滋啦声、刀铲摩擦声起伏,一派热烈,在浓重烟火气中,朱永嘉从容讲述他的故事。
读历史,下苦功夫
“我的生活很简单,我是读书人嘛。”朱永嘉生在商人家庭,父亲是做玻璃生意的。“家离福州路很近,我的零用钱也没有限制,就去书店买书。”1948年,他在上海清心中学高中部读书,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当时爱看鲁迅的书,里面对旧社会的阴暗面揭露得很多,有社会正义感。”1949年上海解放前他就入了党,参加工人运动,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这样的作品也随之慢慢纳入他的视野。
“我的世界观成长在毛泽东时代。”朱永嘉说,“在这个基础上,很自然地接受马克思主义中的唯物主义历史观。”1950年进入复旦大学读书,按照组织安排,两年之后他就开始专注学生工作,成为专职党务工作人员,先后任物理系、数学系支部书记,后来因为健康问题终于在新闻系书记任上退了下来,“太累了,我肺不好,开刀切了一半。”也因祸得福,“在反右中逃过一劫”。退下来之后他才开始专注于业务,“之前都没怎么细读书”。
这之后,陈守实是朱永嘉受益最多的老师。陈守实在中学时就师从吕思勉,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后师从梁启超。“他是很早接触马列主义著作的教授,和我党的关系比较密切了。他的很多观念对我读书很有启发,比如说要了解中国历史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土地’,了解西方历史根本的问题是‘商品’。他专门开土地制度史这门课,还有周予同的经学史史学史,我跟着他们学。”
读历史还是要下苦功夫,朱永嘉根据师长辈的要求,啃下《资治通鉴》这样的大部头。他当时还去北京参加过郭沫若编中国通史的会议。但他认为:“相比较而言,中国的史学系统比西方的要系统、完整,说老实话,读中国历史不能读中国通史,因为中国通史编辑体例从西方来的。你要学的东西是人物,他在特定环境下怎么生存的,他的生活条件、遭遇怎么来的。”
“文革”前后,大起大落
1964年,朱永嘉参加写作组写反苏修的文章,当时组长就是姚文元。后来在学雷锋运动中,他和朱维铮、王知常、吴瑞武等人组成集体创作组,用笔名“罗思鼎”(螺丝钉)发表文章。朱永嘉这样一个普通的历史老师开始步入政治舞台。
如今这些历史痕迹不难在家中书房找到。他家里有一套“文革”期间“上海市委写作组”编选的文艺丛刊,除了那本大名鼎鼎的“石一歌”《鲁迅传》,还有《青春颂》、《朝霞》、《千秋业》等“红色作品”。另外,还有“文革”中的“灰皮书”以及杂志《学习与批判》、《摘译》(分自然科学版、社会科学版)等。这些都是在朱永嘉主持之下编写的。“‘文革’中,所有的刊物都停掉了,小说创作要想办法恢复,因为拍电影要有小说,我们就试着搞文艺丛刊,后来编辑出版了,还有社科类的一套书。”他回忆说。
“文革”末期,朱永嘉先是隔离审查,而后是判刑。隔离审查的时候,家里的书基本都被抄走了,“都送到宣传部了,后来不知去向”。他让母亲给他买一套二十四史,外加一套棉毛裤。“这套二十四史跟着我到过北京秦城,到过上海提篮桥,至今还在身边。”朱永嘉说,“隔离那么长时间,人家也许很难过,但我在里面系统读书啊,等于面壁修行一样。”
后来陆续带进监狱的还有《资本论》、《史记》等等。狱中,他还给犯人上课,教大专班,“没有这些书就没办法上课”。出狱后,公职、党籍没了,但朱永嘉照样还能去复旦历史系资料室查资料和看书,“他们至今还给我很多帮助”。
读历史要为现实服务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朱永嘉重回书斋,教书整理古籍。《吕氏春秋》、《唐六典》两部作品,是朱永嘉最看重的。译注《吕氏春秋》为他打下学术基础。之后做《唐六典》花了五年的时间,大约二百八十万字,“过去没有人整理过《唐六典》,我有了这个基础,做工作就方便了。从中央到地方,从税收到军队,涵盖中国封建社会完整的政治体制以及经济体制和人事制度,这样再去看《史记》和《资治通鉴》就活了。我们现在的制度 还 离 不 开 传 统 思维。”
“不要为个人恩怨、得失纠缠不清。”历经风云变幻的朱永嘉说,最近他在重读柳宗元,因为毛泽东晚年看了章士钊的《柳文指要》,就开始重新分析柳宗元。而朱永嘉重新解读柳宗元也不无现实考量,这是毛泽东教给他的“读书方法”。1975年重病之前,毛泽东要上海市委写作组标点和注释了一批大字本的古文,“比如我标点注释《晋书》的4篇传记:《谢安传》、《谢玄传》、《桓伊传》和《刘牢之传》。毛泽东还校对出了我们没校对出来的错误。这些文章都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朱永嘉认为,1972年毛泽东提出“广积粮,深挖洞,不称霸”就是从《明史》中“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衍生而来。“怎么读历史?不是死读书,不只是考证文章,而是充分用中国的文化,落实到怎么样为现实服务上面。”归结到自身,他说:“我八十三岁了,也不会做官了。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没有其他意图了,读书还是要有抱负,为名为利就离开根本目的了。”
朱永嘉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明史研究专家。1931年出生,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曾师从谭其骧、周予同等文史名家。“文化大革命”期间曾担任“上海市委写作组”总负责人。后从事秦汉史、三国史、明史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著有《晚年毛泽东重读古文内幕》、《论曹操》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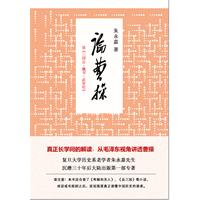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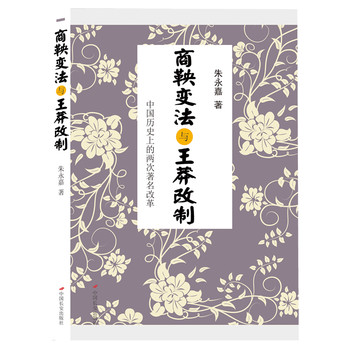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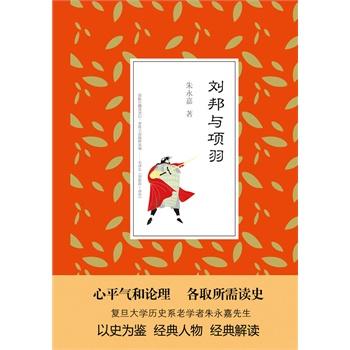




发表评论前,请先[点此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