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抵抗运动”这个略显含混的概念,囊括了三个群体、三种思想渊源乃至它们所代表的道德哲学。军人和文官抵抗者代表对18世纪道德的反思,普鲁士历史上对最高统帅和国家领导人的无条件服从开始被扬弃;法学家和宗教界抵抗者代表对19世纪道德的反思,以法的形式消解法的道德内涵、将宗教隔绝于现世事务的传统开始了自我反思;以“青年运动”为先声的知识界抵抗者则是20世纪新道德的代表,他们以自我学习、自我教育的方式为新德国寻求根基。抵抗本身归于失败,但种子保存了下来,整个战后世界都是其受惠者。
将军与市长:与18世纪决裂
他们痛苦地承认:仅仅坚守本职、不明是非地执行当政者的一切命令绝非爱国,而是民族自杀。
作为抵抗运动中军人和文官集团的领袖,前陆军总参谋长贝克大将(Ludwig Beck)与莱比锡市长戈德勒博士(Carl Friedrich Goerdeler)可视为“老普鲁士”两大支柱的化身:当腓特烈大帝在18世纪为现代德意志国家设计内核时,以服从为准绳的军官团和忠于本职的职业官僚就是其中的基干。这两个群体在1871年曾被俾斯麦用来支撑霍亨佐伦王朝的第二帝国;1918年的耻辱性战败后,又是军人和官僚一同平息了极左、极右两派的暴动,创造出魏玛共和国这个全新政权,使德国可以重新在欧洲立足。
然而将军与市长也有不知所措的时刻:当前二等兵希特勒乘着大萧条的东风,以民众支持和有效的基层组织为工具,通过议会选举这一合法途径对魏玛共和国发起冲击时,他们选择了沉默。这场“市民战胜士兵”(Der Sieg des Buergers ueber den Soldaten)的革命把曾经的支柱变成了配角,军人与文官躲回他们18世纪的硬壳,把希特勒当成腓特烈和威廉皇帝的替代物加以侍奉。希特勒也曾给予他们回报:军官团得到了废除凡尔赛和约、再武装和对法国复仇的机会,文官们则在一个疆域大大拓展的“大德意志帝国”中如鱼得水,这足以使他们对纳粹政权的阴暗面保持沉默。
但服从不等于盲信。当处决苏军政治委员的行动和针对平民的大规模屠杀在东线频频出现,当希特勒无视军事规律、以独断专行和异想天开的方式进行指挥,当意识形态的疯狂在深受纳粹党影响的青年军人和官员中频频出现时,老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他们的18世纪道德。他们痛苦地承认:仅仅坚守本职、不明是非地执行当政者的一切命令绝非爱国,而是民族自杀。他们尝试把国家拉回到正轨:取代纳粹党的政治团体开始暗中建立,旨在暗杀希特勒本人的“闪光行动”和“瓦尔基里行动”也开始策划,并在1944年7月20日的未遂政变中达到顶峰。
然而这种抵抗几乎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刚刚挣脱18世纪道德的将军和市长们依然以古老的行事方式进行他们的斗争,他们轻视宣传、与大众保持距离,甚至设想用某个家世显赫的立宪君主取代希特勒。英勇而幼稚的抵抗既未赢得民众的呼应,在盟军一方也得不到信任:贝克大将在720政变失败的第二天自戕,戈德勒和另外几位军事首脑相继被绞死。
法学家与牧师:告别19世纪
当帮凶和义人之间不存在中间道路时,把信仰弱化成个人选择和纯粹知识问题的做法已形同亵渎。
冯·多纳尼律师(Hans von Dohnanyi)与他的内弟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牧师(Dietrich Bonhoeffer)代表的是另外两个抵抗者群体:法学家与牧师。律师和宪法学者把现代性特征及规范治理原则注入了1871年以后的德意志国家,他们是第二帝国时代的新贵,也是短命的魏玛共和国的设计者。当基于形式民主及多党制的魏玛共和国在1935年被“民族革命”(Nationalrevolution)终结以后,法学家们继续以其专业精神为纳粹政权服务。宗教学者和牧师则在极左与极右思潮的震荡中为国民提供精神避难所,但他们恪守启蒙以来的戒律,与现实政治保持距离。
多纳尼和朋霍费尔是“19世纪精神”最杰出的背叛者。多纳尼及其同志最早揭示了现代法学以形式规范取消法的道德及政治内涵这一缺陷——倘若良法与恶法本质上不存在高低,它又怎么称得上正当?纳粹政权以法的形式阉割法的精神的伎俩,在这种思考面前被彻底揭穿。希特勒架空现行司法体系、以国家安全名义遂行政治迫害的劣迹更令多纳尼愤慨,他加入了国防军谍报局首脑卡纳里斯海军上将(Wilhelm Canaris)和奥斯特上校(Hans Oster)的反纳粹集团,广泛搜集党卫队从事反犹活动和秘密屠杀的罪证,并为暗杀希特勒的行动运送炸弹。
朋霍费尔的抉择则更加复杂。德国宗教界远离政治的传统使大部分神学家对纳粹党的暴行齐齐噤声,唯恐僭越了宗教在现代社会中的“合理”身位;但当帮凶和义人之间不存在中间道路时,把信仰弱化成个人选择和纯粹知识问题的做法已形同亵渎。温文尔雅的朋霍费尔走进了他自言的“窄门”,不仅为汉斯·绍尔(Hans Scholl)兄妹的“白玫瑰”组织提供帮助,还曾亲自前往瑞士与英美情报人员接头。这位曾经的“认信教会”(Confessing Church)成员在1940年有机会出走美国,但他留了下来,直面自己对祖国的责任。
多纳尼与朋霍费尔没有逃过7·20事件后的恐怖报复。多纳尼在1945年4月8日就义于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朋霍费尔则在第二天清晨和卡纳里斯、奥斯特一同牺牲在弗洛森堡。在他们身后,德国宗教界依旧为朋霍费尔在反纳粹运动中的角色争执不休,这意味着朋霍费尔在其遗著《做门徒的代价》和《狱中书简》中的思考不仅没有过时,还需要以新的形式继续下去。
传统的新生:“青年运动”的遗产
“青年运动”的浪漫派色彩和行动主义理论更多地强调个体性,因之一度与崛起于草根的纳粹党纠缠在一起,共同反对高傲保守的军官团和容克贵族。
如果说前两个抵抗集团对应的是历史要素,那么“青年运动”(Jugendbewegung)反映的便是寻找20世纪新德国精神的努力。这场始于上世纪20年代的文化运动直接针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破产和魏玛共和国市民社会的涣散,其载体是“全德青年团体联合会”和成员超过500万人的各种社团。年轻人们读尼采的哲学、斯特凡·格奥尔格的诗歌,登山、野营,演出民族音乐和戏剧,倡导简朴的生活方式、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以及青年之间的兄弟情谊。
不同于德国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思想传统,“青年运动”的浪漫派色彩和行动主义理论更多地强调个体性,因之一度与崛起于草根的纳粹党纠缠在一起,共同反对高傲保守的军官团和容克贵族。但在纳粹的褐色浪潮转变成专制和反人性力量之后,“青年运动”转而向历史寻求答案,成为清廉、尚武、爱国等传统价值观的捍卫者。1944年7月20日试图炸死希特勒的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上校(Claus Schenk Graf von Stauffenberg)正是“青年运动”的精神领袖、诗人斯特凡·格奥尔格最后几位弟子之一,军人家族的荣誉、英勇果敢的贵族道德和热爱真理的品质在他身上得到了完美体现。
同样受到“青年运动”影响的还有大学生汉斯·绍尔兄妹领导的“白玫瑰”组织,他们在1942年就提出了战后德国全民反思的基本问题:希特勒的崛起不是一个偶然事件,知识精英应当为他们对魏玛共和国的背叛和助纣为虐承担责任。“白玫瑰”组织印发的传单提出了“反抗暴政”、“重建德国”的口号,在绍尔兄妹1943年被捕牺牲前起草的最后一份传单中,全德国的生者都听到了这样的呐喊:“德意志民族正看着我们,期待着我们像1813年挫败拿破仑一样,在1943年的今天,以我们的精神力量来挫败纳粹主义的恐怖政权。”对传统的重新发现和维护,佐证了大历史学家梅内克(Friedrich Meinecke)在《德国的浩劫》中的颂扬:“在德国军队里、在德国人民中间,依然有一种力量不愿意像哈巴狗那样的屈服,而是具有殉道者的勇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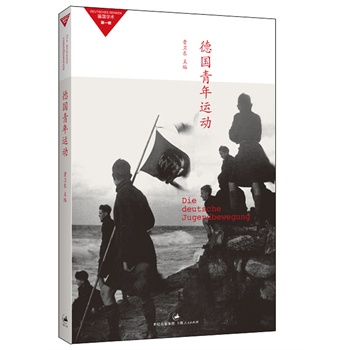






发表评论前,请先[点此登录]